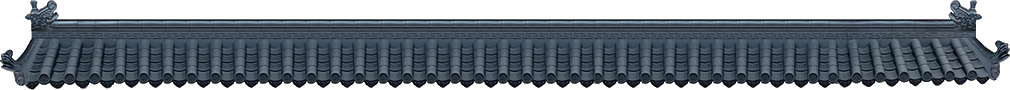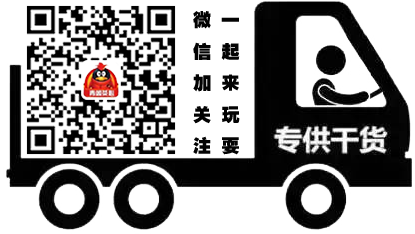眼睛丢了_青春校园_!
我会在每个我到过的海边取那里的水 当我看到我的哪瓶海水干枯的时候 就会回到那个地方 去重新寻找当年还没来得及找到 或者,已经逝去的东西。 ——《我们还有梦想》栏目小组 1. 沿途张望,心被一阵风扫下的落叶拍得感伤。窗外的风景,落叶如雨,一个孩子大叫:妈妈快看,叶子,叶子。那声音柔得像丝。 我不由得望向窗外,那些不知名的叶子模仿生命旋转坠落,就像我们曾经那些破碎的健康向上的小理想那般可笑,只有活着才最严肃。我的眼睛是用来洞悉梦想,一个世界上,每个人的梦想。但世界终究纷繁混乱,肉眼看见的世界每天都在变,看见的过程才是静止。每根神经都不揭穿它的特质,像时光一样,把我们身边的一切都带走了,不过都是些皮毛,带不走的都已经种在我们身上,但没有名字。 我已不是朗眉星目的优雅少年,日光冷清,穿透树枝的缝隙洒在脸上,每缩一下脖子,便会有一点微薄的暖意传来,我已无动于衷,麻木着渴望被温暖同化。 T校的同学都说我另类,说我总去徐悲鸿艺院门前对着那尊雕像祈祷,嘴里还念念有词,像在朗读一段不可告人的咒语。室友老笨也对我说,你无论在哪,比如浴池、公交车上、电影院、白塔公园等,你的嘴总像诵经一样,真应该去医院看看,去神经科看看。特别喜欢我的聂老师也说我变得不可理喻。 很多同学都问我为什么,我不想说,因为没有问题的回答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我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向学校请了病假,称自己患了高尿酸血症,尿酸高得是常人的三倍,俗称痛风,不是不能上课,但只能躺着上。 回到平城,奶奶家还是那样温暖。床睡时间久了,我更喜欢躺热炕,这也是爷爷一直不习惯搬进楼房住的原因。四奶奶也把我奶奶家当成免费的疗养院,她的腿脚不利索,时不时的也来躺一下午,说这样对她的腿有好处。她每次来都带着一些新闻,或者是一两件新鲜事儿。今天也一样,她说“二十迈”家的房客,那个刚成年的体型较大的小伙子因煤气泄露中毒死在市医院的抢救室里,这是没碰到明火,若碰上后果更不堪设想了。奶奶边听边咂嘴,“唉唉”地直呼可怜。 爷爷也说,天然气和数字电视早就应该普及到咱们这了,该淘汰的就淘汰,就像这件事,要早换成天然气就没这事了。我爷爷读过几年私塾,不像奶奶那样漠不关心时事。 “二十迈”是我中学同学钟晓帅的舅姥爷。他走路的样子很滑稽,上半身向前倾,所以走路速度十分惊人,比“永久”慢也慢不了哪去,都说能接近二十迈。这个绰号是和他一起来平城的知青们叫开的。 他自己也经常操起电话:“喂,您好!我是二十迈。” 2. 九六年的某个夜晚,空气仿佛在一夜之间突然萧索,天空飘起孤零零的雨滴,很散落。北方的六月就这点不好,雨下得频繁,但量都不是很大,像星陨,都能数过来,至少有那么几次,你会数着它下了多少分多少秒。 金叶就是从那个夜晚开始憎恶雨水的。 我和金叶都在厂办小学就读,所有的学生均来自职工子弟,唯独金叶和弟弟金晓虎不是。这是一所相对封闭的学校,里不出外不进,金叶的父母又不是职工,所以同学都开始胡乱猜测,说她家一定和厂办领导或是李校长家有关系,或者是蒋副校长的什么偏亲,要不怎么会收她入校? 教室也从那时起滋生一种叫猜疑的味道,久久不散。 其实,又有谁见过她父亲总是提着大包小裹的水果、瓜子和花生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学校。他平时很少说话,但这几次却不惜讲述自己的不易来换取同情,李校长上任若干年来从没碰过类似的事情。 校长的原则也被自己的恻隐层层渗透,良心倍受怜悯的怂恿,只好无奈地搞个简单的投票仪式,学校里那几个挑大梁的校领导也自然明白他的良苦用心。 金叶的记忆中,父亲一直摆地摊儿炒瓜子卖瓜子,卖各种各样瓜子和花生,父亲的手套没有一副是完整的,总是磨得支离破碎。班里的孩子都疏远她,谁也没有见过她的母亲,所以一群十来岁的孩子总是抱起团儿排斥她,甚至背地里无耻地称金叶为“瓜子生的”。 有的孩子还将双臂放到头顶模仿瓜子分裂状,模仿她从中间蹦出来,真让人难以置信。多么龌蹉的称呼和动作,竟来自一群十来岁的孩童,可见当时的前进小学是个什么样的资质。 但金叶从来不生气,她从小到大就没生过气或者和谁辩解,她知道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自己梦想能考一所理想的大学,梦想金晓虎的心智能和正常人一样健全,弟弟这一生都会很幸福。即使母亲早就有了新的家庭,父亲在母亲眼里是那么的窝囊,可这个干瘦的男人是那样爱着自己爱着弟弟,每想到这些,她又觉得自己是个骄傲的演员了。 我送她一只玩具狗,她为它起个名字叫“大海”。金叶把它拴在教室中间靠着她的玻璃窗下沿儿,无聊时候就用手指去弹“大海”的肚皮,随着她无聊次数的增加,“大海”也就愈发活跃。 那是我表姐去云南旅游时给我带回来的,尖尖的耳朵,没有鼻子,暗红的眼睛更像狼,有点搞笑,她特别喜欢,我就在她生日时送给她了。 好长时间我都怕同学们在背地里嚼我的舌,为这事我还后悔了,但这却是她在班级里收到唯一的礼物。她后来告诉我,当时的她只有两个朋友,一个是狗,一个是我。 3. 低年级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总上楼找金叶告状,说金晓虎又把谁摔倒了,一碰到这种事,她就立即下楼向人家道歉,又向双方班主任赔不是。然后就会引起老师和同学们的不满,一件事情重复发生难免会让人腻味。再然后,她又趴到书桌上垂头丧气地去弹“大海”的肚皮了。 金叶最高兴的一天,我记得特清楚,那是前进小学每年度都要举行的仪式,一群健康活泼的精灵们成为少先队员,由我们高年级的学生为他们系红领巾。也赶巧,我和金晓虎面对面,我把这块圣洁的东西边折叠边系在他的脖子上,这块三角红似乎能驱散邪灵,当然,这是迷信的解释,可金晓虎居然表现出格外的驯顺。我回头看了一眼金叶,她在笑,她的笑像一团儿晴朗的云朵,好美。 她在小长城的瞭望台上哭了,对于她的哭我只能尝试着回忆。 放学了,天空一直飘着碎雨,金晓虎又把人摔倒了,金叶已然顾不上他,她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奔向父亲的摊位,帮父亲将十几种干果收回住所。 被金晓虎摔倒的小男孩沾了一身泥巴在那里哭,他还是不依不饶,我实在看不下去就上前拽了他一把,他反到冲我来了,小笼包一样的拳头砸向我,一边哭一边将鼻涕在我身上胡乱地蹭。我的眼睛开始放红,更像“大海”的眼睛,我一个巴掌打在他脸上,他哭得更凶,他边哭边伸手抓地上的泥巴往我身上抹,我被他抹得像个泥人愣在那。他的脸上已经凸起我的指痕,旁边的同学都在笑,笑得很爽朗。我的大脑一片空白,但最后还是把他送回家了,应该算是拎回家的。 晚饭后,我的同桌银铃给我送来一大包瓜子,说是金叶给我装的,还说让我把脏衣服换下来拿去给她洗,我问她金叶怎么没自己来,她说不清楚。 至于我和金叶怎么去的小长城,过程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是冬天。 大概是我想带她看看我们平城唯一被历史遗留的产物。那里面有湖,有跑马场,有坦克,有瞭望台。她在瞭望台上哭了好长时间,没有缘由。我不敢问她为什么,但我猜想应该跟她父亲和弟弟或者“大海”有什么必然联系。 回来时,星光遍洒,人像活在三明治里。明晃晃的夜空和雪地夹着黑色的表情与空间,我们谈了各自的理想。金叶的理想是赚很多很多钱为弟弟治病,哪怕是最基本的不再找人摔跤。我当时的理想当然是出于某种目的,我说我想有一个女朋友,还要有一把吉他,我想在小长城的瞭望台上为我女朋友弹吉他。 太晚了,金叶说,你要能用雪为我建造一个温暖的小房子,并且永远不融化,我就做你的女朋友听你弹吉他。 那好吧,我说,我们去南极。 这是我们最深入的一次接触,也是她这种女孩儿在那个年龄段唯一的一次放纵。可这种最简单最愚蠢的对话都无比唯美的纯真年代必定会一去不复返。 因为这个世界,没有不融化的雪。 4. 小学毕业我们就分道扬镳了。 我直接进了平城中学,金叶去了教学质量不是很好的Y中。听钟晓帅讲,她父亲的干果生意每况愈下,她们家也只好搬出前进小区,住进了房租更廉价的“二十迈”家的厢房。 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是说不敢相信奶奶和四奶奶的对话,这是阳春三月的光束和零下几度的干冷天气仅有的一次冷暖骤然的交替。 事实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命数,没错,这就是生命。可它偏要在多少泪水和殊途的一堆白骨上经历一段经历,去经历别人的生命。 这件事给我带来极大的沉重感,感觉自己像被手臂般粗细的绳子缠绕,恐惧在沉睡中还伤春悲秋地怀恋自己的流光水逝,无声无响。睁开眼,看见的全是不知名的丑陋的嘴脸,有我的,也有别人的,忽又变得迟疑。 我来到前进小学,想拾起童年的欢乐,但这里已经没有认识我的人。校园像一座荒岛,已被个人承包住满了租客。操场被一条条晾衣绳织就成铺天盖地的大网,校园的红围墙已有多处破损,未经修缮的教学楼更散发起陈旧的味道。这个时候,只有傻瓜或者百无聊赖的人能帮我回忆,我曾经和谁并肩走过,唱过,大笑过,谁或谁。或者一群人坐成一字排,双手拢在嘴边大声唱:唢呐铃铃,喇叭嘟嘟。 十年,恍如隔世,总是滚开了再回来才不想长大。曾经的孩子,每只蝴蝶,每滴水或者水中的瓦砾和藻类都已经历一场青涩的道别。 我感觉这片操场再也不属于我,或者是任何人。 5. 据小道消息,初三上学期,金叶与Y中教代数的何老师(数学组男老师,外号“大河马”)发生一次大举动的争吵,之后便辍学了。还有另一种说法,说她是有目的,她想出去打工赚钱,赚很多很多钱为金晓虎治病。 世事难料,有些想象会瓦解回忆,因为再也不敢去想。有些笑是真的笑,但不纯粹。有些痛更是真的痛,不在肉身,却司空见惯。这应该就是T校的老师和同学绞尽脑汁想在我身上获取的答案,只是我浑然不知。 《十诵律》曰:人有四种,粗人、浊人、中间人、上人。唯独我不能分类,我只是个会缅怀的人,是个戏子,仅此而已。也可以说是个嫩芽在固执地坚守,坚守着一段过往抑或一个真实。 我的大脑不断涌现出曾经的梦想,每个阶段的梦想。小学时的梦想只是每天能吃十块话梅糖或者我家开一个玩具厂。中学就更离谱了,想有个结实的腰带,腰上佩戴两个东西,一个树叶刀,一个ZIPPO。 如今的梦想才是真正的梦想,想一切都不失去,例如童年。可有些人的梦想已逐级消逝,就像船的断裂,船上的梦,纤维,描写,一切的一切已没了色彩。 一个病入膏肓的会各种各样游泳技巧的蒙斯托拉斯,岸边和口粮怎么能等同呢? 虽然这么形容很离谱,但至少要找个方式证明,就像一个人去尝试生食就是想证明返祖的静态异变;豆蔻是一个烟雾弹,来势迅猛,终被挤压、被液化成一个躯壳;记忆像青春痘一样,长大了也就消失了。只有血管最为锋利,能破开坚冰,能创造一切。 回T校的火车上,小男孩摇着熟睡的母亲。妈妈,叶子,快看啊,叶子。 他眼里的了然都是像我这样看多了世事的人所看不到的。我独自来到T校的人工湖,趴在白玉状石器上低头看湖面和湖里的自己,我的肌肉接近松弛,口水砸向湖面,一滴,两滴,如过期的被倒掉的半瓶解百纳。 湖面像一个蔑视者的笑容荡漾开来。 谁也不知道她的轨迹,也许像一片叶子,即便停留也只为欺骗你的眼睛。我成了盲人,看不见眼前那些美丽的茶花,一朵两朵,一片又一片,开了又落。 我想和叶子对话,想朗读,但终于没了力气,只会念一种没有主题的经。能发音的,只是被怀疑的语无伦次的妥协。 我很无耻地偷听到一段巫师的向心咒,听不懂,只能如奉纶音地抄袭。大概是说,我的眼睛丢了,即便它有另一个名字,双眸,仍旧在视野中迷失。
上一篇:最后的大学生活_青春校园_!
下一篇:高三,心灵的灯塔_青春校园_!
本站源码和一些文章收集于互联网如有侵权或其它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以便及时处理!